2021年12月,柳叶刀委员会首次提出“重度自闭症(Profound Autism)”的自闭症亚型分类,并建立个性化和有差别的护理支持体系。
在认可神经多样性的主流趋势下,这个概念的提出,有振聋发聩的力度。它意在自闭症这个广泛的谱系里确定一个准确、简洁和有意义的定义,这无疑会让更多人正视重度自闭症的生存困境,将康养资源向更需要社会支持的重度自闭症患者倾斜。
相对于重度自闭症作为弱势群体的呼声,轻度自闭症家长的压力、焦灼、求助似乎更多。他们的孩子夹在NT与自闭症之间,他们更渴望孩子“变得正常”,更在意是否读普校,在意孩子能否考到好成绩,任何细节没做好就会愧疚、自责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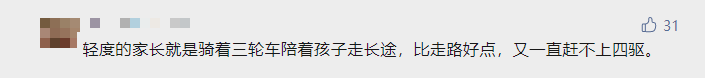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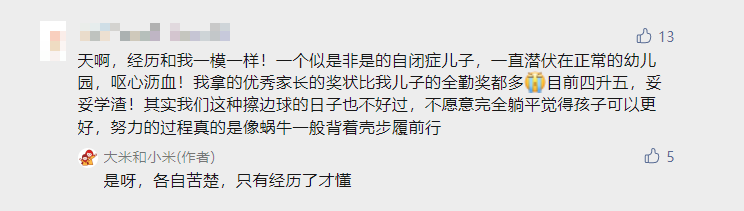
轻度自闭症家长的留言
这些诉苦被一小部分重度自闭症家长认为是“矫情”——“你的孩子都会说话了,还能上学,还有什么愁的?”
为何会形成这种反差?轻度自闭症家长的焦虑该怎么“破”?小编整理了几位轻度自闭症家长的经历,为家长们提供参考。
白白耽搁的“黄金干预期”
比起重度自闭症来说,很多轻度自闭症孩子因为症状较轻,通常语言能力尚可,认知理解能力正常,只是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交障碍、兴趣狭隘、刻板行为等等,更容易“混入人群”。而当家长发现时,往往已经错过“黄金干预期”,问题比初露端倪更加严重,家长更容易因此陷入愧疚和自责中。
中轻度自闭症孩子MM曾经让妈妈十分困惑。
MM8个月大的时候,妈妈和奶奶发现MM不会用手指物、应名有问题,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互动之后,她的发育大标准跟上了:会叫爸爸妈妈、会认识物品……MM妈喘了一口气,然而到了2岁半,MM依然停留在1岁多的水平。
MM3岁时按正常年纪入园了,没几天,老师就发现,MM不听指令,自理不行,语言弱,集体活动总是跑开,喜欢一个人玩,在她耳边喊她名字,都不理。
种种征兆之下,MM妈才终于带MM到中山三院求诊,邹小兵教授确诊,MM是自闭症,在轻度到中度之间。
出于侥幸,MM妈依然继续让MM上了半年幼儿园。但是就因为这段时间“放羊”,MM从中轻度掉入中度。
半年间,MM妈已接到老师多次投诉,MM的状态也越来越差,几乎不说话。最后老师明确告知MM妈, 孩子只能上半天幼儿园。MM妈这才带着孩子做住院评估,评估报告显示,MM已经是中度自闭症。MM妈再也无法欺骗自己,承认孩子的状态已经跌入谷底。

葫芦喜欢在公园里“放空” 图源:葫芦妈
有些阿斯患者甚至到了十几岁才确诊,比如大小米报道过的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葫芦。葫芦到了初二才确诊,但其实,早在葫芦读小学的时候就有许多异常情况,但那时父母并没有注意。
葫芦小时候,父母只关心他的成绩,只要没考好就批评责备,他语文经常不及格,父母批评他粗心大意,而从来没有想到葫芦并不擅长这种学习方式。葫芦小时候会挤眉弄眼,父母就呵斥他站好,不要故意这样做,但后来才知道,这是抽动症的表现,不是故意的。
一次,葫芦在院子里高兴地玩,说作业都已经做完了,却被爸爸发现有几项漏做了,就大加训斥:“以后没做完作业不许出去玩!”
这些错误的教育方式,都是葫芦在确诊后他告诉父母或者父母意识到的。有一次葫芦妈对他说:“这些事情放在你心里这么多年,沉甸甸的,真难为你了!”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“跪着进”普校
把孩子送进普校是所有轻度家长计划表中的重要一关。因为在中国,特殊学校接收的大多是残障人士,而轻度孩子往往能够通过早期干预得到有效提升,普校就承载了轻度家长让孩子成为“正常孩子”的期望。
与此相对应的是轻度自闭症孩子“入学难”的问题,每个进入学龄阶段的孩子家长,都需要经受普校的审视,反复权衡孩子入学的现实问题。即便孩子成功入学,他们也会在各种忧虑和焦灼中挣扎,不断咀嚼、咽下孩子与NT之间不留情面的差距。
2019年的暑假,皮皮爸准备带7岁多的轻度儿子皮皮入读公办小学。然而这个暑假是皮皮爸在儿子确诊后过得最焦虑最灰暗的一段时间。皮皮已经超过入学年龄一年了,让他在校园之外多待一分钟,皮皮爸就多一分钟揪心。
皮皮爸费尽周折,想把他送进一所有融合干预资源教室的公办学校。但是皮皮却把入学前的面试搞砸了,他在教室里东摸西转,屁股上似乎装有陀螺,无法安坐,老师发出指令,他听得懂,但就是不照做,还一直喊那位40岁上下的老师叫“奶奶”。“奶奶”在表格上为他写下一行定论,“建议到特殊学校就读”。看到那张A4纸,皮皮爸的眼泪都快涌出来了。
皮皮爸把皮皮送进了一家机构设立的暑期班里,每天上下午7个多小时强力干预。从第二天起,老师不断反映他的进步越来越快。一周之后,他基本可以安坐,并听从老师的指令,一个多月后,他顺利通过了划片小学的面试,拿到了录取通知书。那张大红的硬纸攥在手里,像是一份喜报,也像是一封开庭审判的通知书。
果然,在开学第一天的下午皮皮爸还是迎来了儿子入学后的第一次约谈,反映皮皮不听指令。此后,皮皮更是问题不断,无法安坐,几乎不说话,成绩也完全跟不上。

大小米报道过的自闭症孩子一一,是一位预后非常好的自闭症孩子,2岁时确诊典型自闭症,经过一年半的密集干预,3岁半时,已经“达到了最佳干预效果”,几乎“摘帽”。6岁时,被医生评价为“社交、沟通能力和其外部环境已达到和谐的平衡稳态。”
到了6岁半的时候,因为一一的表现几乎与正常孩子无异,一一妈决定要给她找一个重点小学,以后才能有更好的未来。那时候一一妈天天想着怎么让她超过其他孩子。焦虑的情绪无处释放,一一妈忍不住对孩子发脾气,导致一一每天都哭着写作业。
因为客观原因,一一最后没有进重点小学而是在一家村小就读,为了让一一适应学校,在入学前一一妈做了很多准备,调整作息,练习写作业,熟悉校园环境,一一都完成得很好。
然而,到了真正开学的时候,一一很快又表现出了问题,上课走神,爱哭闹,其他同学拿走她的东西她大哭,玩游戏没有赢也大哭。一一妈又开始新一轮的焦虑。
“螺旋式上升”的悲与喜
皮皮爸发现,皮皮的进步是“螺旋式上升”的状态,“他总是遇到瓶颈,上一个台阶遇到一个瓶颈,再上一个台阶又是一个瓶颈。进步的同时,麻烦也越来越多,这是并行的。”
这种“波动”是轻度家长经常提到的关键词,比起重度更能够维持“稳态”,轻度的孩子波动更大。
因为总是波动,轻度孩子总是处在正常孩子和自闭症孩子的临界点上,家长们一直身处“不进则退”的压力下,总是希望孩子可以离“普通孩子”再近一点。这样一来,孩子的任何风吹草动,都会加重家长的焦虑。

皮皮刚入学的时候,总是一个人玩,很少吭声,甚至有同学认为他是个哑巴。为此,皮皮爸还专门做了一个视频介绍皮皮的生活,在班会上给全班同学看。但是升入四年级,皮皮开始对同伴交往产生兴趣,变成一个话痨,这让皮皮爸很欣慰,但同时,他惹麻烦更多了。
皮皮喜欢抓女生的辫子,还跟其他同学学了骂脏话、竖中指,看到别人因为他的挑衅哭或者生气,他觉得“很有趣。”
他上课就走神,下课就闯祸,几乎一天一个麻烦,每次皮皮爸拿起老师的电话就会条件反射地说“抱歉”、“对不起”。皮皮爸觉得皮皮就像普通孩子问题的“变态版”。
他和弟弟都有一块小天才手表,两个人兴冲冲地加了许多好友,但没过多久,他发现很多同学都把他的电话删了,弟弟的手表里却还有很多人的名字。皮皮有了嫉妒的情绪,他直接抢过弟弟的手表把列表里的好友全部删除了,惹得弟弟大哭。
皮皮爸知道这是不对的,但他没有批评皮皮,至少比起原来那个木讷呆滞的学生,皮皮现在更像一个活泼灵动的孩子了。
留下三分余地
圈内知名自闭症家长凯爸认为,很多时候家长对孩子失望甚至绝望,根源在于对孩子期望过高。
他以倒茶为例,他发现对待许多能力较高的自闭症孩子,大多数家长的教育态度就是“茶满杯”。家长根本不清楚或者是没能力把控好孩子的“上限”,一厢情愿地按照自己的想法,去勾画所谓美好蓝图,直到把孩子“烫到”,承受不了“崩溃为止”。
因此,家长要站在尊重个体的基础上,重新认识和定位孩子的状态,调整对孩子的期待。
在一一频繁被老师投诉的时候,一一妈开始反思自己对“自闭症”的理解,每个孩子都会走神,都会哭闹,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一的“专属”。她选择忽略孩子身上自闭症这个标签,直接面对问题,见招拆招。
她在家里模拟学校课堂,还经常和孩子一起读绘本,结合绘本给一一讲道理。她不再害怕问题,而是去探究问题的原因,“问题出现是干预的最好时机。”她发现一一铅笔和橡皮都有图案,吸引她在上课时走神。于是她给一一换了没有图案的文具,一一走神次数果然变少了。

在得知葫芦患有阿斯之后,葫芦妈开始反思自己之前对待儿子的严厉态度,倾听孩子的声音,找到适合他的学习方法。初中开始,大班教学不适合葫芦了,初三和高三的升学季,她就让葫芦请假不去学校,自己请辅导老师来教,学习效率提高了,每天还能有更多时间自由活动。
中考结束后,葫芦考得并不好,经过几个月的心理斗争,爸妈下定决心让他报考职中。葫芦妈说:“如果让他活下去和升学之间做选择的话,我肯定先选择让他活下去”。
现在回头看,葫芦妈觉得葫芦上职高是最正确的选择。在学校创设的宽松环境下,葫芦状态越来越好,最终还考上了大学。现在,葫芦已经大学毕业,会做午饭,锻炼身体,还经常更新公众号,他还不乏浪漫,会在夜风吹拂的窗前弹琴和画画。
葫芦妈不急于给他找工作,而是带着葫芦到欧洲游学,只要他“能够参与社会生活,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,过得平安充实就足够了”。
一开始,葫芦妈和大多数自闭症家长想法一样,想要辞职陪伴孩子,但在好朋友的提醒下,她意识到“只有你自己的状态恢复,才能够有精力去面对孩子。”她一直保持着工作,一边赚钱,一边给葫芦购买更好的干预服务,让葫芦有更好的生活条件。她学习自闭症的专业知识,练习正念冥想,定期做心理咨询,这些事情就像把她捞起来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凯爸曾经总结自己对自闭症儿子凯凯的教育:“星儿干预七分力,留下三分是余地。”这里的“余地”,既是干预的力度,也代表生活的松弛与平衡。
只有“有恒”,生活才能持续。







